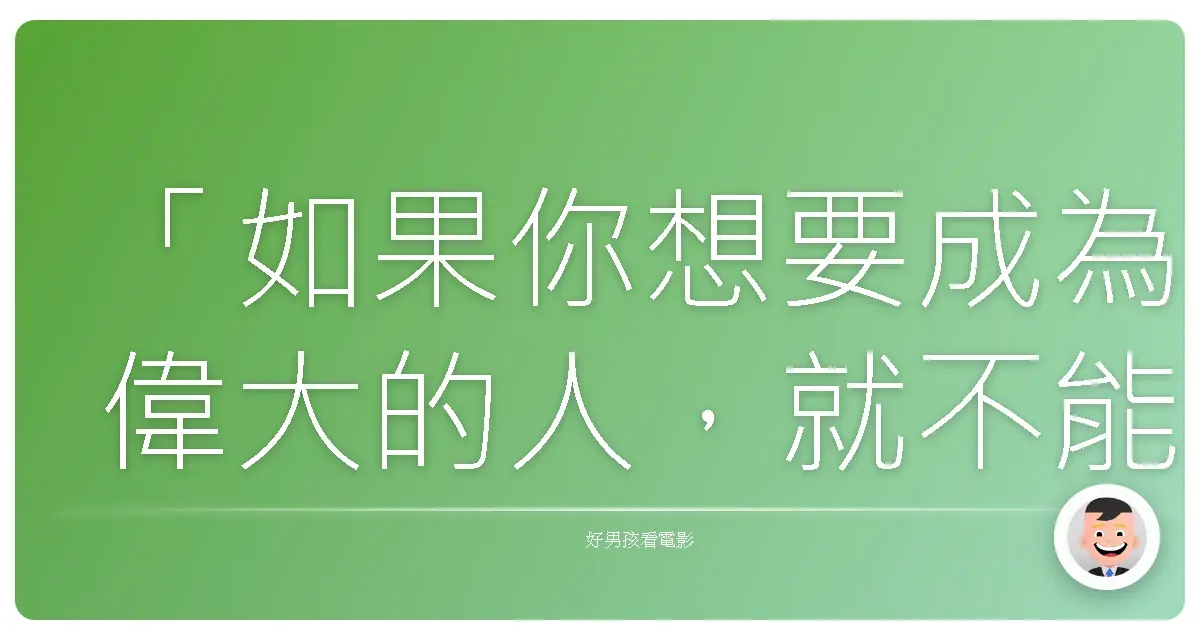
「如果你想要成為偉大的人,就不能只是好人。」《爆裂鼓手》(Whiplash),2014
《爆裂鼓手》是一部讓人一邊心跳加速、一邊咬牙切齒的電影,它不浪漫、不溫柔、不留情,但卻像一顆釘子,狠狠釘進我某段掙扎中的生命片段。這部片我其實已經重看好多次了,每次心情不同、狀態不同,看完後的感觸也都不一樣。它不像某些電影那樣會撫慰你,它只會無情地把你拉進焦慮、拉進壓力、拉進極限的邊緣,然後丟下一句話:「你要不要繼續?」
我一直記得片尾那段瘋狂敲擊的鼓聲,不只是音樂,那根本像是一場暴力的對話。是一個人對自己說:「我不要只是這樣了。我不要只是那個 ‘還不錯’ 的人。」
說實話,我曾經是個很愛當「好人」的人。你知道的,懂事、貼心、不惹事、不麻煩別人。職場上配合度高,朋友之間誰需要幫忙我都點頭,連生活裡遇到陌生人請求幫忙,我也都說:「好啊。」久而久之,我習慣了壓抑自己的感受,只求別讓任何人失望。久了,就變得麻木了,甚至連自己到底要什麼都搞不清楚。
直到有一段時間,我開始夢到我自己在舞台上演奏,但我彈的是鋼琴,台下沒有觀眾,燈光全打在我身上。我彈得很快、很用力、甚至有點崩潰,但夢裡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與瘋狂,那種感覺,好像才是真的「我」。而當我在某個失眠的凌晨重看《爆裂鼓手》的時候,我突然懂了,那根本不是音樂的夢,而是我內心深處一直壓抑著的渴望──想被看見、想突破、想狠狠活一次。
這部電影最讓我痛的是,它不講成就,它講代價。主角不是天才,也不是英雄,他只是個為了想要更好、更厲害、更接近完美的「某種樣子」,願意付出一切的人。連人格、連人際、連健康。他的老師也不是什麼溫暖的引導者,而是一隻獵犬,盯著每一個潛在的獵物,咬住、逼出他們的極限,不擇手段。
看到主角被丟椅子、手指流血、整個人幾乎崩潰的時候,我反而不是感到「好可憐」,而是心裡某個地方被震了一下──我也曾經在自己的人生裡那樣過。我曾經為了一份工作,把每天變成熬夜與責罵交織的煎熬;我曾經為了一段感情,讓自己變得不像自己,只因為我怕失去。但那不是突破,那是消耗。
電影裡最讓我震撼的是一場演出前的崩潰與重生。那個時刻,我們都知道他已經「夠了」,真的可以放棄、可以回家、可以擁抱一個普通的生活。但他選擇站上去,打出一場讓人屏息的鼓聲,打到老師眼神從「你完了」變成「你贏了」。那不是在對老師證明,而是在對自己說:「我值得。」
我後來也問自己很多次,我到底要什麼?要舒服?還是要突破?但這問題不是一刀切的選擇題,而是我逐漸學會認清:我可以選擇什麼時候要當那個瘋狂敲鼓的人,什麼時候回到溫柔的日常。
生活並不總是讓你選擇當個「偉大的人」,有時候連當個「好人」都很辛苦。但《爆裂鼓手》提醒我,人生裡有一些關鍵時刻,是你必須放棄好人的身份,勇敢得有點自私、有點不討喜,只為了那個更靠近真實自己的版本。
你有沒有那種時刻?就是你也想站起來、走向舞台、把心裡的節奏狠狠敲出來的時候?
我記得有次我跟朋友聊起這部電影,他說:「那主角最後雖然贏了,但他也失去了很多東西耶,這樣值得嗎?」我當時答不出來。但後來我想了一陣子,我想他其實並不是失去,是他用那些「原本不屬於他的東西」去換了一次真正屬於自己的高光時刻。那也許很短暫,但卻是自由的、火熱的、誠實的。
這部電影後來對我來說,變成一種檢視:我還有沒有在為了別人定義的「好」而活?還是我能不能,再給自己一次瘋狂的鼓聲?也許你不用真的流血,也不用真去學鼓,但你心裡有沒有什麼聲音,是你一直壓著沒讓它響出來的?
有次我看完這部電影,立刻寫了封信給自己──不是什麼雞湯文,而是我真的對自己說:「我可以做選擇,我可以選擇現在不要討好任何人,只聽我自己的聲音一次。」
那天,我哭了。但那是我真正開始為自己活的第一天。
所以,如果你問我,《爆裂鼓手》到底好不好看,我可能說不上來。因為它不是讓你「喜歡」的電影,它是一部讓你全身刺痛、然後開始動起來的電影。
一部不是拍給觀眾看的,是拍給你心裡那個「還想更多」的自己看的電影。
而如果你也曾經害怕過、逃避過、壓抑過,或許你會懂,
有些時候,我們敲響鼓聲,不是為了掌聲,而是為了不再沉默。